犀利姐陈文茜-凯发会员官网
阅读提示:那个曾经在街头激情演讲的年轻人虽然退出了政坛,在书中,依然像街头一样犀利。
记者|何映宇
犀利姐。这是记者对台湾著名主持人陈文茜的第一印象。
说话直接,毫不客气,指东打西纵横捭阖,思路清晰滔滔不绝,也难怪李敖称她为“我所见过最聪明的女人”。
3月25日,她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,可是和她对谈,你会有一种错觉,似乎她还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作为台湾政坛中的风云人物,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数十载,从民进党的宣传部主任到愤然退出民进党,起起落落,看尽其中的猫腻,陈文茜点评那些台湾政坛的大佬,嘴下可从不会留情。
这一次到上海,陈文茜是为她的新书《树,不在了》签售。“树不在了,但新的树在哪儿?”陈文茜在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。树,在这里指的是人类曾经积极拥抱过的两棵参天大树:“资本主义”和“全球化”。这两棵遮天庇荫保护的大树,却在一场金融海啸面前叶落花残,呈现枯萎之态。
怎么办?树,还在吗?当老树已凋残,遮蔽我们众人安然的新树,又在哪儿?

如果你以为陈文茜的新书是一本心灵鸡汤类的随笔集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个曾经在街头激情演讲的年轻人虽然退出了政坛,却仍然关心着社会发展的运态,在书中,依然像街头一样犀利。
飘零的种子
《新民周刊》:你的外公何集璧曾参加共产党,也参加过“二二八”事件,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有没有受到迫害?
陈文茜:非常严重的迫害,他当时的心情很痛苦。所以我写他的文章,题目是“飘零的种子”。他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的富商家庭,当时台湾割让给日本,他家里人希望他去日本念医生,他不愿意成为二等公民,到了日本跳船往中国大陆跑,第一站来到上海。之后又去北大,在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他的富商爸爸听说他参加了共产党,骗他说自己死了,发了个讣闻让他回台湾奔丧。他一回来,他们家人就把他扣留。1931年大萧条之后,他在台湾建立了文化协会,他的立场还是替当时失业的劳工争取权益,文化协会的大会宣言也是他写的。当时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办了一份杂志叫《台湾文艺》,这是台湾第一份文化杂志。由于他是士绅出身,当时反对日本人的台湾人也分成右派和左派两个阵营,他属于调和者。为什么?因为他是有钱人的小孩,士绅都挺他,但他的老板是左派。所以他就到山上找了一个在山上砍柴的文学家,就是杨葵,来做《台湾文艺》的总编辑。
等到二战结束,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,他是很欢迎国民党的。我妈妈还记得,当时他带着全家的小孩,穿着皮鞋,家庭条件还是不错。只是后来,国共战争把整个台湾都卷入通货膨胀,经济很差,去台湾的军队,素质又很不好,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,民众就起来抗争。“二二八”之后,他被抓去坐牢。按理说他不是枪毙就应该给关很久很久,因为他涉入这么深。当时整个台中的左派,就在我们家酒楼的二楼开会。我外公家原本是开纺织工厂,他就开了个酒家,当时的文人喜欢在酒家里聚会,有点像当年的秦淮河畔。他用他的酒家来掩护这群人的活动,这是很严重的罪名。在那个时候,没什么罪名的人都被杀,他被抓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怎么办?只好用钱贿赂,还好国民党有贪官,我们家把整个纺织工厂都给他,将我外公定为精神病人,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关押了好几个月才让他回家。从此他就落落寡欢,沉默寡言,又感染了肺结核。肺结核会传染,他似乎成了家里的一个不祥之物,家里所有的小孩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,说起来是为了保护孩子,可是那种不祥的感觉,好像超越了病菌。他经常会在夜里哭嚎、尖叫,害怕有人抓他。他也很自责,因为他的好朋友都在坐牢。
《新民周刊》:后来你到台湾大学读法律系以及之后的从政都有受到你外公的影响?
陈文茜:他给我的影响,就是:社会就是我的职业。刚开始考法律系出于社会抱负,后来才知道,法律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loyal跟个买办差不多,人家付你钱让你去办事,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。我去了当时最大的报纸《中国时报》副刊当主编,开始与民主运动有关系。当台湾开放党禁之后,我就加入了反对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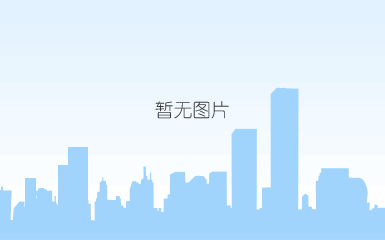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些人与政治的关系,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关系。所以当政治变成权力计算的时候,也就是我们离开政治的时候,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,其实所有的问题都问错了,他要知道我们参与政治的原因,跟别人不太相同,对我们来说,政治是你如何投入、建构一套制度的行业。当这种理想建构到一定程度,一定会遭遇世俗化的进程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就会与世俗政治格格不入,那也就是你要离开的时候。不管你能力多强、名声多好,你占了怎么样的位置,政治的中心和你的价值观就已经格格不入了。
《新民周刊》:你是觉得所有的政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,还是仅仅只是台湾的窘境?
陈文茜:不管什么制度的政党,一党独大的像新加坡,或者是美国似的民主,收买政治都很严重,政治家要讨好老百姓。在讨好的过程中,它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会不同。浪漫主义者从政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吧。
陈水扁与马英九
《新民周刊》:就你的了解,2004年的“三一九”枪击案是陈水扁自己炮制的吗?
陈文茜:这个没有人知道。我们只知道一个讯息,这个讯息是当时奇美医院一些重要的人告诉我的,我无法告诉你这些人的名字,因为我一说出来就等于害了他们。他们告诉我,陈水扁当时是走进医院的,当时到底怎么发生枪击案,奇美医院其实也不知道,医疗团队都是他自己的,只是借用奇美医院把手术做完了。13:45发生那么严重的枪击案,枪击的伤口那么长,你想想有多痛?他的侍卫长说给他擦了小护士药膏。因为里根遇刺后是自己走进医院的,所以陈水扁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领导者也应该自己走进医院,可是你走进去也应该是很痛楚的表情吧,他不是,他就这么轻松地走进医院了。你看吕秀莲膝盖中枪,痛苦的样子,被随从背进医院,你就知道她应该是真的。
有一种可能性,陈水扁进奇美医院之前确实有枪伤,可是身上打了麻醉药了,所以他不觉得痛。这是大家从医学角度看。没有人知道枪击案的真相。我们只是确切知道,他是走进去的。后来我们就要求他怎么进医院的录像资料,奇美澄清他们是清白的,可是那已经是选举后了,造成的影响已经来不及挽回了。他已经把社会都玩弄完了。
《新民周刊》:你刚才说的是陈水扁执政,现在是马英九执政,你觉得情况是不是有所变化?

陈文茜:马英九也是世俗政治,也不是我所喜欢的政治人物。只是说两个人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是不一样的,陈水扁我们刚刚讲完了,如果你要问我马英九的话,他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办法做自己。看马英九现象,对很多个人一定是很好的启示录。第一句话是:“if you want to please everybody,please nobody.”(如果你想取悦每个人,就是所有人都得罪光。)我们常常开玩笑说,马英九可能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,但马英九也是个没有朋友的人。像我讲话属于比较直接的,我要么讲真话,要么沉默,所以我应该还是比较会得罪人的。可马英九怎么可以得罪那么多人?可以制造那么多敌人?怎么这么多人恨他?我们也算佩服他。这也很需要政治能力耶。坦白讲,像我这样一个算直率的人,很容易因为不小心的语言,或者某些我的坚持得罪人,挡了人家的财路,可是我也不会到他的一百分之一。他是怎么得罪人的?我到现在也是衷心地佩服他。
第二点,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,最终没有人要相信他。马英九以两岸和平的角色崛起,他大选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历史定位,连战来大陆是“破冰之旅”,马英九是60年来唯一一个可能稳定两岸关系的(台湾)政治领袖。从1949年至马英九上台2008年,整整60年,他是第一人。怎么定位这种和平,让它的基础很稳定?结果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。为什么?他故意用一个李登辉的幕僚来做“陆委会”的“主委”。他的意思是:这是本省人哎,他是李登辉的人哎,所以我没有出卖台湾。一个人,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,结果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。他的政策,连大陆都觉得莫名其妙,两岸关系应建立更好的和平架构、更深入的经贸架构,都不断被阻挡,搞得支离破碎,就因为这个“陆委会主委”,他的理念,根本和马英九最初上台时理念是两回事。
马英九教我们的第三件事是越想抓住权力的人,失去权力越快。他已经当到这个位置,可是他的行为还是蒋经国秘书的行为,什么事情都想抓。他完全是不避讳。他只用他的亲信,对社会充满了怀疑。他抓紧了权力,怀疑所有的人,包括国民党内部,包括连战、吴伯雄,怀疑他们每个人都出卖自己。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政治领袖能像他那样“兵败如山倒”。
讲给所有的意见领袖听
《新民周刊》:2010年的香港书展,你关于韩寒“浅薄没文化”的言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当时怎么会说这番话的?
陈文茜:那次争论应该说是媒体创造的争论。当时的情况是,韩寒在我之后的一天来香港书展,有媒体就问我怎么看韩寒现象,其实我根本不了解韩寒,我知道他很帅,他是个赛车选手,我知道大陆年轻人很喜欢他,对于他的了解,我也仅限于此。所以我没有什么理由评论人家的好或者不好,并不是我跑到香港去骂韩寒。当时方舟子提出韩寒的小说是代笔的,很多人认为我是反韩寒,也应该加入揭发韩寒的行列。但是我没有,我是学社会学的,我知道那么多年轻人喜欢韩寒,必然有他们的理由,我也不会说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,说他好或者不好,我会从社会现象的角度看它。
那次的争论是这样来的,我们提到上海世博。世博之前的上海,交通一塌糊涂,就因为到处都在造地铁,195个车站,十几条地铁,疯掉了,可是你知道纽约之所以会成为纽约,伦敦之所以会成为伦敦是因为什么?我在纽约住了差不多9年,我也常去伦敦,我很清楚,这两座城市的城市建造者在一开始就已经设想好了,这里将成为世界的中心。所以它们的地铁什么时候造的?100多年前。上海世博呢,等于是补足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第一件必要的大事。盖地铁的过程,市民会有怨言,交通拥堵情况加剧,到处塞车,再加上当时浦东要动迁,就有人上访,据说还有个老人因此去世,美国有一个很恨中国大陆、故意丑化中国大陆的记者,他就写一篇报道,引用了韩寒的话,说:“上海世博是给外人来看的,和上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所以我反驳的其实是韩寒此时说的这句话。我觉得上海建地铁对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。地铁、黄浦江整治、虹桥枢纽,这是一个大格局上海的建设。你们上海人现在在享受这些成果,你就知道你当时忍受的那些痛苦值不值得。上海交通不够好,可是如果没有新造的那些地铁,你看看是什么情况?地铁盖得好,是国际都市名片的第一步。我们还需要第二步,再多盖十条地铁的话,上海的交通会比以前更好,现在上海地铁的总公里数已经超越了伦敦,可我觉得还是不够,中国人口毕竟还是世界第一。
我常常说,不管什么社会,最后都要成为公民社会,但前提是,公民要有知识,要有眼界,否则公民发出来的意见,怒吼越大声,越会把社会往后拉。你看台湾,台湾的情况就很清楚。我为什么会拿这些事情来讲?因为我看台湾已经看得太清楚了,台湾有民主的制度之后,所有的建设都停止下来。这不是我相信的民主体制,它不应该如此。发生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?这是因为太多人,以讨好民众的方式——或者对问题不了解——不负责任地讲话。所以我对韩寒说的是:以你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,你应该珍惜你的影响力,然后把上海带向更好的未来,而不是做这么错误的批评。可是我看媒体写我说“韩寒放屁”,这好像不太是我会用的字眼。
《新民周刊》:所以你的话是对所有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说的?
陈文茜:不是只有年轻人,而是对所有的意见领袖。
※凯发会员官网的版权作品,未经新民周刊授权,严禁转载,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